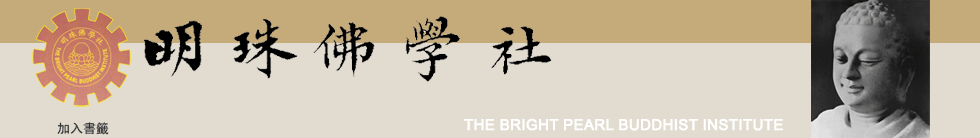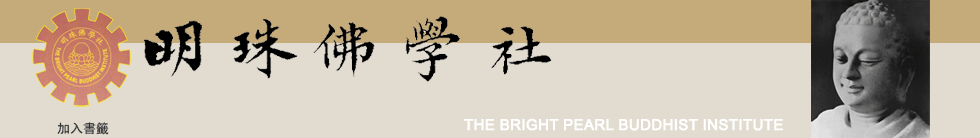第七屆佛學經論研習班(1998-2000年度)修業報告
學員:陳啟賢
試比較《妙法蓮華經》與《小品般若經》之異同
《妙法蓮華經》與《小品般若經》同為印度大乘佛教的經典,並均成於大乘運動發展時期,把它們的思想重點和所要對應的問題作出比較,便能對大乘佛教,有更深入的了解。大體而言,《小品般若經》著重開示般若思想,以「破」為主;而《妙法蓮華經》則透過「一佛乘」,「會三歸一」,開示方便法門,顯露宗教的包容胸懷,以「立」為務。這兩經一立一破,剛好象徵了大乘佛教的福慧雙修,慈悲與智慧兩路並進的精神。本文便環繞「破、立」這兩個重點,及其對部派佛教所作的回應,討論一下,再談談兩經的寫作手法及其影響。在進行分析前,且回顧大乘運動的背景,以便對《小品般若經》與《妙法蓮華經》所要對應的問題,加深理解。
一、 大乘運動
凡文化發展,都經過開出,發展和異化的過程,在一連串的變化中,要不斷吸收、融合、革新、方能保持其生命力,而且與該特定時空內的社會訴求關係密切。佛滅後五百年,印度在政治上,經過阿育王統一全印的黃金時代後,國土淪回分裂狀態,互相吞併,再經歷了案達羅和笈多王朝,雖說是大致上維持了統一局面,但北印度卻長期受外族入侵,生靈塗炭,群眾渴望被拯救的心理要求日盛,大乘經典的開出,「後五百歲」和「五濁惡世」的流傳,與此不無關係。同時,案達羅和笈多王朝都崇尚婆羅門,雖然並無排斥其他宗教,佛教為了持續發展,遂漸漸向下層群眾傳播,爭取支持,並符合他們的心理渴求。由是,一場宗教改革的時機終於成熟。要接近群眾,較直接的方法就是和部派佛教(主要是經院佛教)劃清界線,創造新的理想和標準,除了出家眾,更要吸引在家眾。故此,先破後立,便是早期大乘運動的發展形式。
二、 對應部派 有破有立
早期的大乘經典,都特別著重菩薩行與其他小乘部派的分別,此傾向以般若系統尤為明顯。在《小品般若經》『初品第一』中,開宗明義就提出成就般若波羅蜜的奧義,就是對「我不見菩薩,不得菩薩,亦不見、不得般若波羅蜜,當教何等菩薩般若波羅蜜?」持有「不驚不怖、不沒不退」的態度。這種針對部派,特別是說一切有部,認為所有事物均有相對應的指涉體,一切法皆有其自性的實在論,先來個當頭棒喝。接著,以「不分別心」貫穿聲聞、辟支佛、和菩薩道,如斬瓜切菜,蕩相遣執,一破到底。
從般若思想發展看來,強調「無分別」是般若經的特色之一,在『釋提桓因品第二』,須菩提又指出眾生如幻如夢、佛法亦如幻如夢、涅槃亦如幻如夢,把小乘部派對佛法涅槃恆存,而其他事物如夢如幻的執著,再行否定。《小品般若經》這種推理風格在其他的大乘經不斷發揮,而最致極的要算是《維摩詰經》,其中最著名的『入不二法門品第九』,以各菩薩列舉諸般法門,分析各種垢,淨、一相,無相、善,不善、有漏,無漏等對立觀念,在本質上都無分別,然而最究竟的法門卻是默然無言,超越一切語言,文字和思維,方可成就最高智慧。由此可見,《小品般若經》在佛法的承傳上,起著超越部派,開展大乘的角色,尤其在演繹般若思想中「無分別」的意義上,有所發揮。
般若思想的另一重點,就是對「空」的體會。由於原始佛教對「諸行無常、諸法無我」的定義,留下相當空間,部派佛教徒各自演繹,形成對相、對我,對法的不同理解。其實,如果以「我空法有」(即否認本體,肯定條件)來概括部派對「空」的詮釋,還是稍嫌籠統,單是上座部的承傳,就有不同見解。上座部以為現在法實有、過去和未來法則無(法有空有無);犢子部則施設「補特加羅」的「有分心」(有我);而說一切有部由於堅持無論有為法和無為法皆「法體恆有」,三世亦實有,所謂「只空我執,不空法執」,以上觀點,都是對原始教理的片面理解,故成為大乘所要破斥的對象。
《小品般若經》的『釋提桓因品第二』以空觀,先破五薀:「不應住色,不應住受想行識」;再破無常,無我等觀點:「不應住色若常若無常,不應住受想行識若常若無常…不應住色若我若無我,不應住受想行識若我若無我」;最後甚至於破空觀:「不應住色若空若不空,不應住受想行識若空若不空」,把空的意義儘量深化。另外,在『嘆淨品第九』亦說明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的方法,就是「知一切法空如響,如是亦不分別,當知是為行般若波羅蜜」。
反觀《妙法蓮華經》以「開權顯實」為宗旨,並強調一佛乘,以包融聲聞,緣覺、菩薩三乘,但在法理開展上,並未加深化。雖然在『安樂行品』中提到菩薩摩訶薩「觀一切法空,如實相,不顛倒,不動不退不轉,如虛空無所有性,一切語言道斷,不生不出不起,無名無相,實無所有,無礙無障,但以因緣有,從顛倒生故說」,也點出空的性質,可見其受般若經典所影響,但只作略為平面鋪陳,並未深化。反而,因全經強調「一佛」為「實乘」,若以般若思想的標準看來,便不徹底。《妙法蓮華經》之所以成為大乘佛教的最重要經典之一,因它以容納大小二乘為宗旨,故不見鋒芒畢露的破斥之辭,而代之以大慈大悲的「方便」胸懷。其實,《小品般若經》的『魔事品第十一』亦有提到「方便」:「我於般若波羅蜜中廣說方便,應於中求」。這兒所說的「方便」,只是指一種智慧,與《妙法蓮華經》所指的「方便」,不盡相同。
概言之,兩經之所以散發截然不同的氣質,因《小品般若經》著眼於求道的過程,而《妙法蓮華經》則強調求道的目標所致。但是,若以一破一立的簡單二分法以來形容這兩部經,又未免過份籠統。因為《小品般若經》雖然以觀空,破執為主,未有對一乘和佛陀身份等有所發揮,而以般若精神,力倡菩薩道,著重實踐。但其破執的過程,由破而不立、破即是立、到以破為立,亦有相當正面意義。反之,《妙法蓮華經》雖然表現出廣大的包容性,但在世尊宣說一乘奧義前,還是有五千增上慢人先行離座,這暗示此經的包容仍有保留,亦可見當時大小二乘爭論之烈。
三、 由學佛到成佛
現在的佛弟子都知道,學佛的最終目標是將來成佛。但是,這想法在部派時期可謂不可思議。自《阿含經》以「我生已盡,梵行已立,所作已辦,自知不受後有」為目標以來,沙門都以自身解脫為大方向。直至大乘興起,隨著菩薩道的開展,逐漸把求道者分為三乘,互爭長短。而大乘諸經在面對小乘部派的態度,亦有改變。大乘起步時,為了破舊立新,衝突尤烈。《小品般若經》的初品提到菩薩惡知識,定義是「教令遠離般若波羅蜜使不樂菩提,又教令學取相分別嚴飾文頌,又教學雜聲聞,辟支佛經法,又與作魔事因綠,是名菩薩惡知識。」在『魔事品第十一』,世尊明確指出「當來世或有菩薩捨深般若波羅蜜,反取餘聲聞、辟支佛經,菩薩當知是為魔事」。另外,又反對只會酌字斟句的經院佛教徒,「以文字示般若波羅蜜義,是故汝等勿著文字。若著文字,菩薩當知是為魔事」。凡此種針對小乘修行目標的批判,不斷出現,而且於其他般若經也屢見不鮮。說到「三乘」,其實《小品般若經》的『大如品第十五』也有提及,「如是三乘(聲聞、辟支佛、佛乘)中無差別,若菩薩聞是事不驚不怖不沒不退,當知是菩薩能成就菩提」。表面上雖說三乘無分別,其實是運用雙重否定句,再三指出他們並非究竟法,破小乘人對修行道路的執著。
直至《妙法蓮華經》,從方便出發,配合佛陀住世最後一天的重要關頭,再經舍利弗以印度傳統至尊貴的三次勸請,於是,佛陀以超越三乘的高度,說一佛乘,論爭才出現突破。更說明開佛知見、示佛知見、悟佛知見、入佛知見的成佛四階段。這宣佈在當時可謂空前,因為在部派佛教徒看來,眾生修行當以阿羅漢,脫出三界為究竟,從未想到會成佛。《妙法蓮華經》開接受聲聞乘人成佛的先河,全經的前半部,從『譬喻品第三』開始,就一一替舍利弗(因其智慧第一)、摩訶迦葉、須菩提、摩訶迦旃延、大目犍連等十大弟子授記,他們在將來均會成佛。及後,是五百弟子,另外是學,無學等二千徒眾,各自將來都得成佛。而其中更重大意義的要算是在『提婆達多品第十二』,為提婆達多和龍女授記。眾所週知,提婆達多在很多佛教徒的眼中可謂無可救葯,他不但不聽佛陀教誨,反而想加害世尊,使佛身出血,可以說是罪大惡極。另外,依據印度文化,女性比男性是次一等的(有五道障礙),如果女眾要成就解脫,必須先轉成男身,如此,非要長期努力修行不可。但龍女卻「忽然之間變成男子,具菩薩行,即往南方無垢世界,生寶蓮華,成等正覺」。這不但顯示佛教的平等觀,而且進一步說明求道,成道並無什麼先決條件。此說和《維摩詰經》的『觀眾生品第七』也有類似之處,散花天女與舍利弗的精彩對答,不但打破以男身或女身修行的成見,還把般若思想發揮得淋漓盡至。
龍女、聲聞乘人與提婆達多均可成佛,顯示《妙法蓮華經》在修行的目標上,開拓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廣闊空間,亦描繪了更終極的境界。這個理想的圓融和包容性,足可統攝三乘,形成一種普世救渡的宗教精神。可見《妙法蓮華經》較諸《小品般若經》和其他般若經典,在求道的目標和慈悲的宗教精神上,確有很大突破,並補充了大乘佛教,對於消弭三乘之辯,挽救佛教進一步分裂,貢獻良多。《小品般若經》雖未曾對佛性加以發揮,我們仍可在其『嘆淨品第九』中,尋得一點線索。全品由舍利弗一連串對淨的問題,帶出一切本淨,眾生本來亦清淨,都含藏將來成佛的可能性,其理論卻未夠徹底。及至《妙法蓮華經》明說一乘,加上佛教倡導四姓平等,表示「人人皆可成佛」,才把「佛性」理論化。後來的《涅槃經》更清楚說明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,開展「如來藏」。
四、 佛陀身份
普遍認為,從對佛陀的懷念,到崇拜佛塔,進而產生累世修行的菩薩觀念,是大乘佛教運動的另一原動力。《妙法蓮華經》倡導「一佛乘」,令它與《小品般若經》和其他般若經典不同之處,就在深化和廣化佛陀的救渡精神上。如果把整部《妙法蓮華經》分為兩大重點,以『從地涌出品第十五』為分水嶺,前半部是「開三顯一」;而後半部就是「開近顯遠」,指出釋迦的身份,並不單是活在印度八十年的聖者,而是在無量世以前,早已成佛。這創見可溯源於人們長期處於對佛陀的追思狀態,一方面把時間立體化,產生過去的燃燈佛、大通智勝佛和未來的彌勒佛;一方面把空間立體化,產生東方妙喜國的阿門佛和西方淨土的阿彌陀佛;及後來的華嚴教主毗盧遮那佛,以無量光明遍照十方世界,於是,佛遍佈虛空,而眾生亦全部均可成佛,此說與一佛乘互為表裡。而《妙法蓮華經》的『如來壽量品第十六』更開展出永恆的法身和現世的色身概念。世尊在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以前,經已成佛,他以太子身份在印度出生,成道皆為方便,對眾生示現成佛之路,教化利導。如來壽命無量,教化無量,方便亦無量。
『如來壽量品第十六』的另一創見就是說明佛陀入滅的意義。「若佛久住於世,薄德之人,不種善根,……若見如來常在不滅,便起憍恣,而懷厭怠,不能生難遭之想」,指出「如來難見」,希望眾生把握學佛時機,勿生退轉。這概念直接影響到《涅槃經》。後來中國佛教在「判教」時,便把《妙法蓮華經》、《華嚴經》和《涅槃經》視為最重要的大乘經典,位置最為崇高。
表面看來,在闡述佛身這個概念時,比較《小品般若經》與《妙法蓮花經》,無論在質在量,差別都很大,影響力亦不可同日而語。但是佛陀常住不滅的想法,可追溯至原始佛教中說的「見法如見我」;世尊快要入滅時,還在告誡弟子們要「以法為師」。由於法常住,諸般若經又開展「法即佛,佛即法」的看法。直到《妙法蓮華經》才把法身說系統化,於是佛陀由皈依的對象,變成永恆的象徵,這可算是由對佛陀懷念所展開的一段長時期反省的里程碑,而諸般若經在其演變中的角色,亦不容忽視。
討論至此,大致上已經把《小品般若經》與《妙法蓮華經》的內容重點,有何破,有何立,一一陳述。它們雖然同屬大乘,但因旨趣一在智慧,一在宗教精神,各有重心,看似相差甚大,但細察之下,仍有相互印證,在理念上互為借用的地方。由破到空,由空體會心淨,由心淨到佛性,一脈相承,亦見當時大乘運動在學理上,諸經互相影響,有取有捨,而匯流成一個龐大系統的過程。
由於兩經的思想重點不同,其寫作特色亦有相異之處,以下就作一比較。
甲、 破執之路
《小品般若經》既以破執為主,故特別重視思維,而且自成一種獨特的辯證法。在『初品第一』,提到「不念行般若波羅蜜,不念不行、不念行不行、亦不念非行非不行、是名行般若波羅蜜」。從法理而言,上述這種「相遣法」(雙向否定法),在般若系統中不停運作,其作用是針對事物存在的可能性,加以邏輯分析,作進一步推演,並排遣和消解的一切的可能性。之所以這樣做,是要改變人們的慣性思維。一般而言,我們在攝收外界事物,形成認知過程時,一定會以非此即彼,非彼即此的對偶模式,來定義一切現象,加以分辨而構成知識。然而,這卻正是形成對名相和概念執著的源頭。
事實上,「相遣法」並非佛教所獨創,究其傳統,是印度人早已經對「無」(數學中的零)的概念,有所體會。《吠陀》和《奧義書》的「無」不是指沒有內容,而是一種非存在的狀態。在《吠陀》《無有歌》中,說宇宙還在原始階段時,既沒有「無」,也沒有「有」。這說法與般若思想的「非有非無」相類似。當然,若在法理上予以區別,則《無有歌》是指一種實體的「有與無」,而般若的「有與無」,是指消解對「有」對「無」所起的概念,對象並不相同。總之,印度文化很早已接受了「無」的意念,及至原始佛教時期,其他外道亦有本著「有無相對」的原則,有所發揮。根據《沙門果經》,我們可以找到「相遣法」的原型。主張虛無主義的思想家散若夷說:「現有沙門果報,現無沙門果報,現有無沙門果報,現非有非無沙門果報」,可以算是運用對破,以貫徹其懷疑論的邏輯推理。其分析手法與佛教的很相似,但佛法是建立在「緣起性空」的前提上,以消解執著為目的,並非只流於文字推理。故此,以上散若夷所證,只屬戲論,背後並無真理支持。
由於《小品般若經》能掌握「相遣法」的箇中竅門,超越慣性思維,達到破執,效果則十分顯著。所以自《小品般若經》到後期的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,也一直沿用不絕,亦成為般若經典的寫作特色。
乙、 救渡之路
我們在《妙法蓮華經》內,找不到像《小品般若經》的精密思辯,因為前者所提出的「一佛乘」,就是指出諸法都是為方便教化而設,法本無高低之分,只是工具,若有眾生稍經點化,便可悟佛知見,便是利根;否則窮經數十載,還未見法者,仍為鈍根。為了能對應不同根器的弟子,便大量借用譬喻,深入淺出地宣說教義,這對「非專業修行」的在家眾,實在適合不過。著名的「法華七喻」雖然各有旨趣,大體上都是暗示佛陀以長者或嚮導的身份,作各種權宜方便,或鼓勵,或吸引,使兒子,商旅等追隨者發心向上,不斷努力。這種親眾生如父子,向他們施以救渡的方式,是由上而下,顯示極大的慈悲精神。
而《小品般若經》並沒有像《妙法蓮華經》般借用大量故事,說明教理。惟在經末的『薩陀波崙品第二十七』和『曇無竭品第二十八』,以長篇幅描述常啼菩薩「不依世事、不惜身命、不貪利養」,一心求般若波羅蜜的故事,來表示般若難得。並對菩薩智、菩薩觀、尤其是菩薩行的大乘精神,作一總結。就修行的過程而言,《小品般若經》所提及的菩薩道,是一種自下而上,層層破執,乃至拋棄生命亦在所不惜的「難行道」,顯示極大的犧牲精神。這與《妙法蓮華經》的慈悲性格,剛好成一強烈對比,亦可見它們一破一立,一剛一柔的不同風格。
分析過兩經寫作特色之後,下面再討論一下它們的影響。
甲、 開示般若思想
先論《小品般若經》。由於它是般若系統的先行者,處於自部派過渡到大乘的關鍵時期,所以特別強調「破」的觀念。全經不斷運用否定語,像「無」、「非」、「不」、等字眼,指出部派佛教徒過份鑽研一字一句的錯誤。在破的同時,又確立了「假名」和「實相」的概念,如是,發展了般若思想的首階段。其影響之下,後來的般若經典由「破」推論出「空」。這樣,佛教的「空」就由現象(相空),進展成本質(本空)。在般若思想的次階段,依《小品般若經》深化而成的《大品般若經》,詳細分析了「十八空」,就是走這條進路。其後,龍樹菩薩強調「空亦復空」,並發展成「中道」思想,至此,對「空」的思想內涵才大致完成。其實如果將集般若思想要旨的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,所提到的「色不異空,空不異色。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」,和《小品般若經》『初品第一』中的「幻不異色,色不異幻。幻即是色,色即是幻」並置,便可說明般若思想的一脈相承。而《小品般若經》在「空」的發展上,確實擔當了非常重要的起步角色。
除了教義,大乘運動在開展時期所遭遇的,就是經卷的正統問題。部派佛教徒多以「非佛說」來質疑大乘經典的可信性。與之對應,《小品般若經》在全經之始便表明立場,指出「佛弟子敢有所說,皆是佛力。所以者何?佛所說法,於中學者,能證諸法相;證已,有所言說,皆與法相不相違背,以法力故」。此說實在反映了當時部派對大乘的對抗態度,亦由於經此說明,大乘佛教方可在險峻的形勢下,得到紮根的機會。如果無此前提,所有觀點均不攻自破。雖然維護大乘佛法並非《小品般若經》一經之力,但在整個宗教運動的推動上,也起著一定作用。
乙、 發展宗教精神
《妙法蓮華經》晚出於《小品般若經》,所承受自部派佛教的壓力亦相應減低,所以全經的語調也傾向柔和,以吸納三乘,開相容,方便之門。有學者認為,在整個佛教發展的過程中,在《妙法蓮華經》之前,佛教並未能稱為宗教。因為自原始佛教以來,佛法都是一些人生哲理,盡管其對應的都是生老病死的大問題,然而仍欠一種博大包容的救世精神。直至《妙法蓮華經》以慈悲救渡為宗旨,迎合了信眾冀望將來得救的理想,才奠定了佛法的宗教基礎。《妙法蓮華經》的後半部的『分別功德品第十七』、『隨喜功德品第十八』、『法師功德品第十九』、強調信仰和供奉,讀誦和講解此經的好處,並談及信徒所獲得的種種利益,表面上是彰顯佛陀普世救渡的慈悲精神,但若由宏揚大乘看來,此說其實是吸引社會基層群眾的方便手法。例如在『分別功德品第十七』說明「若自持,若教人持。若自書,若教人書。若以華香瓔珞,幢旛繒蓋,香油酥燈,供養經卷」就有「功德無量無邊」而「能生一切智」,像開啟了一個易行而又有豐盛成果的法門,對所有弟子,尤其在家眾十分相應。比諸《小品般若經》和其他般若經典著重智慧,以破為立的推理和辯證手法,《妙法蓮華經》的確能吸引更多信眾,這可以說是宏法手段的突破,並為其他大乘經所借鑒。而此經在傳入中土後,大盛於兩晉及南北朝,及後來一直流行,部份亦由於其講求信仰,強調功德的特色,正符合了中國民眾渴求庇蔭,只望心之所安,毋問佛法奧義的性格。所以一直以來,抄經、印經等善信多不勝數,可見《妙法蓮華經》影響之廣。尤其是『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』,以實實在在的現世救渡為中心,「設入大火,火不能燒……若為大水所漂,稱其名號,即得淺處……」,更有免於羅剎、惡鬼、冤賊之災;求生男生女之妙,所謂「福不唐捐」,所以此品特別受大眾歡迎,以致有把它獨立成篇,受持讀誦。
《妙法蓮華經》除了能吸引大量信眾,宏揚大乘佛教外,在教理上,因強調「一佛乘」,開權顯實,延伸了佛乘思想的涵蓋面,並深化了真如、法性、佛性、涅槃等概念,故此經一傳入中土,便馬上得到僧侶垂青,而大乘各宗都受其啟發。最明顯的首推天台宗,在「判教」上,確認《妙法蓮華經》為最圓滿。四祖智顗著《法華玄義》、《法華文句》和《摩訶止觀》,強調其諸法實相,諸法如是,提出性具三千,一念三千,確立止觀雙修的大原則。而《妙法蓮華經》既以「信」為基礎,其思想是傾向於「有」甚於「空」,此性格與唯識宗相近,所以窺基則著《法華玄贊》,認同一乘為究竟法。另外,《妙法蓮華經》對華嚴宗的教義也有深切關聯,以火宅喻中三車為三乘,宅外一車為一乘,同樣贊成佛乘為最高法,法藏曾撰《法華經疏》,而澄觀則發過十願,其中第五願就是要長誦《妙法蓮華經》。禪宗雖不立文字,但談到心悟,則可轉經,六祖慧能的「心迷《法華》轉,心悟轉《法華》」,就是這個意思。他指出《妙法蓮華經》只講一乘,之所以有三乘,皆因心迷而起。
丙、 各有所本 互補不足
綜觀《妙法蓮華經》,無論在沙門和一般信眾都有很大影響力,其廣大包容精神,納三乘於一,以方便功德,使大乘佛法流佈於天下,所以被冠以「經中之王」,實非過譽。但若以為光受持此經,已可通達佛道,則未免偏頗。修行和讀經雖可一門深入,然而大乘佛學是一個完整的系統,除了法華,尚有「空」「有」二門、華嚴、涅槃諸經,它們的理論互相引援,亦有取捨。《妙法蓮華經》在教理和思辯而言,不及《小品般若經》之深入,對「相」還有所保留,其中如「實乘」觀點,及功德的確認等等。如此,在發揮般若之破執精神尤未徹底。而且行菩薩六道波羅密,當以般若為骨幹,所以無論如何讚嘆一佛乘,如何說誦經功德,若不配合破執和空觀,就是有偉大目標而無清楚航線,愈是努力,可能愈加偏執,由執生見,由見而迷,就離佛道日遠了。故六祖教訓弟子不要以為讀上「經王」百遍千遍,就有無上功德。因為此舉無疑是著於文字,比較之下,與部派佛教徒不斷分析名相,定義心法無甚分別。可是自《妙法蓮華經》傳入後,因符合國人對求道那種捨難行易的性格,著重抄印念誦多於理解,若不以般若智慧觀照,只能算是盲目崇拜,流於表面。與其獨誦「經王」,不如多聞薰習,以開放態度,對其他大乘經卷,多方理解印證,使不著於文字,不迷於章句,行悲智雙修之道。歸之,《妙法蓮華經》和《小品般若經》由於旨趣不同,故可起互相補充之效,均豐富了大乘佛法的內涵,為學佛過程中所必修,必讀。